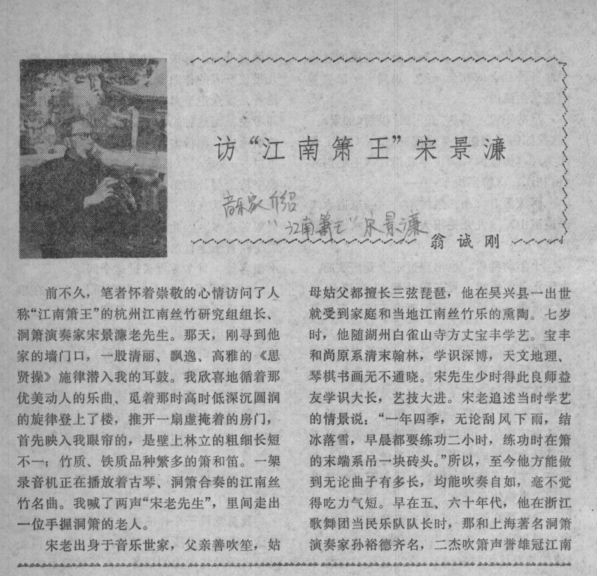翁诚刚先生 发表于1984年 《人民音乐》杂志笫七期
前不久,笔者怀着崇敬的心情访问了人称“江南箫王”的杭州江南丝竹研究组组长、洞箫演奏家宋景濂老先生。那天,刚寻到他家的墙门口,一股清丽、飘逸、高雅的《思贤操》施律潜入我的耳鼓。我欣喜地循着那优美动人的乐曲、觅着那时高时低深沉圆润的旋律登上了楼,推开一扇虚掩着的房门,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壁上林立的粗细长短
不一;竹质、铁质品种繁多的箫和笛。一架录音机正在播放着古琴、洞箫合奏的江南丝竹名曲。我喊了两声“宋老先生”,里间走出一位手握洞箫的老人。
宋老出身于音乐世家,父亲善吹笙,姑母姑父都擅长三弦琵琶,他在吴兴县一出世就受到家庭和当地江南丝竹乐的熏陶。七岁时,他随湖州白雀山寺方丈宝丰学艺。宝丰和尚原系清末翰林,学识深博,天文地理、琴棋书画无不通晓。宋先生少时得此良师益友学识大长,艺技大进:宋老追述当时学艺的情景说:“一年四季,无论刮风下雨,结冰落雪,早晨都要练功二小时,练功时在箫的末端系吊一块砖头。”所以,至今他方能做到无论曲子有多长,均能吹奏自如,毫不觉得吃力气短。早在五、六十年代,他在浙江歌舞团当民乐队队长时,就和上海著名洞箫演奏家孙裕德齐名,二杰吹箫声誉雄冠江南沪浙。
江南丝竹有一个明显的特色,“花、细、轻、小、活”。所谓“花”,即是华彩,“细”则是细巧;“轻”乃是轻松;“小”即是小型;“活”就是灵活。箫在江南丝竹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宋老先生的洞箫吹奏艺术造诣很深:低音淳厚、高音清脆,花指灵动,颤音华丽,高难度的“飞指”、“打音”双、三指皆运用自如。特别是三指打音和姆指的后空打音更为突出。箫的吹奏以扪“1”(do)为最“险”,难于演奏,他却能做到音准而纯。其他几个音也都能熟练地用“扪”法自由吹奏,这当中扪“3”(mi)、“5”(sol)吸收了昆曲的奏法特点,扪“6”(la)吸取了婺剧奏法特点。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宋老先生的“气颤音”,如唇的移位颤音,“历音”(多音符上行或下行级进的装饰音)、“辨音”(非级进的较少音符的装饰音),吹奏起来主次分明,清彻婉转。宋老先生还在继承传统表现手法的同时,勇于创新,如琴箫合奏曲《梅花三弄》,原是晋桓伊所作的笛子独奏曲,后人改编为琴曲时也习惯用笛子搭配,。然而宋老先生改为以箫伴和之,使乐曲低柔优美,别具一格;《西湖风光》即是宋先生在挖掘的基础上,创作的江南丝竹名曲,现已灌制成唱片,流传于海内外;《思贤操》原来也是琴笛合奏的,经宋老改为琴箫合奏以后,加强了低音区效果,使此曲所表现的“思念”情绪更为突出;而在《小霓裳》中他又把“2”(re)音改为“6” (la)音,提高五度以后,曲调更为典雅优美。
宋景濂先生认为洞箫演奏必须“死曲活奏”,这样才能做到引人入胜,曲毕回味浓。他积数十年之经验,总结出《丝竹演奏法要领》的诗文(口诀),它虽来出版,我想对广大丝竹音乐爱好者和研究者极有裨益,现摘其中几段如下:
音准节奏稳,乐曲要抒情,风格须道地,情绪求逼真。
主奏必突出,寡主有分寸,特色力求醇,伴奏多同声。
死曲要活奏,引入能入胜,毕曲回味浓,仙乐修养深。
音韵随机变,主调莫变形,花音必生动,画龙求点睛。
颤音似流水,飞指如腾云,避免发虎啸,和音学龙吟。
寻音求清晰,“弧”音要温情,“历”音上下顺,尽量少滑音。
高音轻松过,低音莫过劲,相互协作好,力求找共鸣。
一忌出噪音,二忌多和声,最忌风格变,更忌无盛情。
花、细、轻,小、活,点点明意境,运用变化活,音里会传情。
会通“精”、“神”、“化”,精益再求精,学用要结合,态度须谦逊。。
平日常薰陶,练功勤且奋,扬长又避短,实践出聪明。
传统须保存;特色要鲜明,“丝竹”可创新,全靠继承人。
这诗是宋老毕生心血的结晶,也是五十多年来他对“美”的追求和探索的总结。
近年来,他整理演奏的乐曲计三、四十余首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台、浙江省电视台、电台,杭州电台录音录像播发,受到国内外音乐界的好评和听众的广泛欢迎。
1983年4月宋景濂先生应邀随中国丝竹表演艺术团去香港演出,数十家报纸报导了他们演出盛况。有家报纸以《花甲老人奏妙曲,百年古乐献知音》为题作了专题报导。有家报纸还誉他为箫笛大王。访问演出归末后,他到北京作了汇报演出,并受到中央领导同志和文化部领导的亲切接见。在京津期间,他曾应邀到清华大学和天津音乐学院讲学和即兴表演,受到了热烈欢迎。
杭州江南丝竹研究组是由浙江省和杭州市专业和业余民乐工作者组织的江南丝竹演奏、研究小组。小组成立四年多来收集、挖掘、整理、演出了一批优秀的传统曲目,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一些新的丝竹音乐作品;他们还接待了美国、日本、瑞典,新加坡,泰国等文化团体进行民间音乐的交流五十余次。研究组为中华民族音乐的振兴、发展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宋景濂先生任这个研究组的组长,当我同他一说起江南丝竹,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清癯的脸宠,显得容光焕发,他说:“我的艺友们大都是省、市剧团或艺校的专业工作者,大家住得比较分散,又没有具体办公地点和固定的活动场所,活动起来是有些麻烦的,我既是活动召集人,又是传达员,一有什么活动就须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去联系,一家一家去通知。我和我的艺友们靠的是‘三合”五心’才坚持至今。‘三合’即情投意合,志同道合,互相配合;‘五心’即信心、决心、恒心、虚心,细心。当然,最重要的是市文联等上级组织的关心”。接着他又一口气告诉我研究组所有成员的大名,并详细介绍了每位成员的专长和演奏艺术特色,看得出来他对所有的成员都怀有很深的感情。由于大家的通力合作,配合默契,故他们的演奏以其古朴,典雅、流畅、华彩的艺术风格和道地的江南乡土:气息受到听众的欢迎。而宋老在为研究组的成立,发展所付出的心血是可想而知的。宋老桌上有一迭书信,经同意,我略略看了一看,写信者,国内国外,专业的,业余的、工人、农民,干部,战士,教师、学生,大多是青年朋友。内容有颂扬的,也有求教的。宋老先生认真地说:“来信者都是在音乐上有追求、有事业心的人或是祖国传统音乐的爱好者,不能让他们失望,我抽空一一作答,时间不够,往往写信到半夜三更,我想,应该对青年后辈负责,应该对祖国音乐负责。”据我所知,宋老退休后的“业余”工作是很多的,近年来宋老先生不计报酬地到工厂、农村、学校、部队义务演出和辅导,笔者也早有风闻,例如有两个春节,他都是牺牲自己过年和亲人们欢聚的机会,带领省春节慰问团文艺演出队赴部队医院和海防作慰问演出的(然而他自己正是气管炎老毛病折磨他的时候);又如:一次到宾馆接待外宾,为外国朋友演奏时却正是他的腰痛病还未痊愈。如此等等……,除演出辅导外,他还经常要接待登门来访和求教者,一位美国康州威士连大学的研究中国民族音乐的副教授唐健恒先生就曾亲自登门拜访,他们一起探讨了中国古典音乐作品的学术问题。由唐先生弹古琴,宋老吹箫,合奏了晋朝恒伊所作的《梅花三弄》呵!真可谓古今音律通,琴箫传情谊。
目前,西子湖畔文艺百花争艳,民族音乐欣欣向荣,宋先生深受鼓舞。他真诚地表示在今后的有限的岁月里,再组织和录制二、三十首江南丝竹乐曲,以实际行动开创新的局面,为祖国民乐事业的繁荣昌盛奋斗终身,把毕生精力贡献给党,贡献给祖国人民和世界人民。